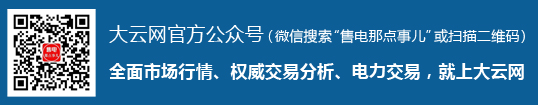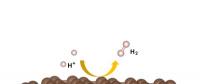裁判可通过大数据预测?

施鹏鹏
2017年,年仅25周岁的法国人路易·拉海-查内设计了一个离婚诉讼结果预测软件,受到了雷恩上诉法院、杜埃上诉法院及里尔律师公会的关注。
离婚诉讼结果预测软件在法国法务市场引发震动
该软件立足已公开的250余万份司法判决,并进行大数据处理,能较准确地演算出法国各地不同类型离婚案件诉讼结果的概率,包括子女抚养权、离婚补偿金数额等。例如,在雷恩,如果女方当事人存在通奸行为,有孩子需要抚养,那么有34%的概率获得离婚补偿金,赔偿金的数额在0.8万欧元到3.2万欧元之间。而且,所提供的情况越详细,演算的结果越精确,越接近司法实务的现实状况。
此软件一经公开,短时间内便有了极高的人气和下载量,可谓在法国法务市场上投下一颗震撼弹,引发了理论界、实务界乃至社会公众的关注。与此同时,支持者与反对者也围绕大数据下可预测的裁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消除地区差异、统一适用法律的有效方式,可恢复公众对司法的信心。例如,里尔律师公会主席斯蒂芬娜·东特便持此观点:“我们同胞真正的问题是有些害怕法院……裁判预测系统或许能够让处于风险之中的他们放心。”此外,裁判预测系统也让法官及双方当事人对诉讼结果有着较准确及清晰的认识,可有效促成法庭调解,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在根本上解决时下日趋严重的法庭堵塞问题。反对者则担心,大数据下的裁判结果预测,可能会产生伦理问题,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有人认为,“人们将通过算法计算危险度,并依可能的累犯率作出量刑。从职业伦理而论,这其实已是科幻小说。”
美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大数据裁判态度略有不同
其实,立足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裁判系统在美国早已有之。例如,美国兰德公司民事司法中心的沃特曼和彼得森曾设计了法律决策系统,主要用于产品侵权责任的预测,通过模拟既定规则的推理模式,可以较准确地比较过失和计算赔偿金。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安德烈亚·罗思新近在《耶鲁法律杂志》甚至脑洞大开地提出了“机器作证”的概念,尝试以“机器”协助陪审团进行证言可信性的判断。法律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在短时间内成为新兴的课题,吸引了大量从事法律、计算机、人工智能、逻辑和哲学领域等人才投入其中,资本市场亦蓄势待发,希望能在合适的时间内进入,以分割庞大的法律服务市场。
但与美国的人工智能热相比,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对大数据裁判显得更加保守。核心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知识结构的差异。的确,与美国的法学教育不同,欧陆法学家普遍接受最传统的法学规范教育。在长达十余年的法科学习中,多数法学家更关注法学领域的热点问题,更多注重规范的解释与适用,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但对于法学以外的领域,多数法学家涉猎甚少,遑论诸如计算机工程、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但近年来,这一状况已大有改观。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司法文化在整个世界主流司法文化中的强势地位以及对欧陆诸国的冲击。一些欧陆新派学者开始探索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例如法学与经济学、法学与心理学、法学与社会学,当然也包括法学与计算机科学。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大数据裁判在欧陆主流的学术期刊或者教材中极少涉及,多数的学者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根本的原因是人工智能可能对传统的一些法治基本原则造成颠覆性的冲击,有些可能还涉及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侵害,优弊的权衡仍需作冷静的思考。
大数据裁判带来三重冲击
大数据裁判首先冲击的是个人信息自决权。所谓个人信息自决权,指公民个人依照法律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决定是否被收集和利用的权利。该权利最早由德国学者威尔海姆·斯坦穆勒和柏恩卢特贝克在1971年提出,并在1983年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正式援引。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大数据,必然涉及对众多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及整理,其中还包括诸多涉讼的隐私信息。例如前所论及的离婚诉讼结果预测软件,尽管开发者多次声明,这仅是对规范关联要素的推理模拟,与具体的当事人、案情、涉讼事由并未有实质关联,但数据库的设立原本便涵盖了案件的所有要素,尤其是特殊案件关键数据的截取,这与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已然构成尖锐的矛盾。即便不考虑数据可能泄露或用于其他商业化的用途,欧洲诸国普遍认同的公民被遗忘权也应得到保障。因此,设立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可能涉及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欧陆诸国普遍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11年便宣布刑事诉讼数据存留违宪,禁止将电信数据作为刑事情报来源。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除特殊刑事案件(主要为性侵害)外,涉案公民的个人信息不得留存,或者应在既定的期限内予以删除。
大数据裁判可能冲击传统的证据规则,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法国大革命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从法定证据制度走向自由心证制度。1808年的法国《重罪法典》曾较为详细地描绘了何为自由心证,“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第343条)因此,自由心证要求裁判者(法官或陪审团)通过案件的亲历性进行综合判断,既可能涉及事实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还可能涉及价值判断,后者是人工智能所难以替代的。即便在事实判断领域,裁判者往往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有效地提炼裁判要素,并准确适用证据规则,这恐怕也是倍受质疑的。尤为有趣的一点是,如果人工智能与法官(陪审团)裁判存在结果认定上的差异,这是否可构成上诉事由。法国已有律师以初审法院的判决和立足大数据的模拟裁判结果迥异为由提起上诉,要求推翻原裁判,要求作出更符合大数据的判决。这一立足大数据的模拟裁判结果,应作何种性质认定,效力如何,可否成为制约法官裁量权的刚性机制,这都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领域,人工智能还将对无罪推定原则造成冲击。为更准确地进行事实认定和定罪量刑,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库必然应存储大量的犯罪案件信息以进行比对分析。可以想象,诸如前科、类似行为、品性等必然成为重要的逻辑结点,影响着人工智能的判断。对此,里尔律师公会主席斯蒂芬娜·东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饶有意味地谈起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所执导的电影《少数派报告》:“未来或许是可以预知的,罪犯在实施犯罪前就已受到了惩罚……但律师必须站在对立面,提醒着人们古老的故事和魔鬼。我们是否离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少数派报告》并不遥远……在许多公司所觊觎的约十亿欧元的交易市场下,这些伦理问题应及时得到解决时。”
大数据裁判的深度思索
当然,人工智能在当下及未来所带来的冲击势必是深刻且遥远的,必将远超我们这代学人贫瘠的想象力。但在热浪滚滚、群情激奋的当下,冷静的学术思考亦必不可少,因为当“阿尔法狗”碰上“独角兽”,结果或许不仅是理想状态中“智慧”与“正义”的简单叠加,而涉及社会价值判断、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因素。学术研究是没有禁区的,我们完全可以探索人工智能之于法律决策的辅助甚至将来的替代功能,可以思考互联网上的虚拟庭审和远程裁判,可以研究“机器作证”中的证词可信度评估,但司法裁判却涉及公民的权利、自由甚至生命,理应作更充分的论证及更冷静的判断,不能在想象中尝试,亦不能在躁动中迷失。
在科幻的世界里,无数的小说家和影视作品试图临摹一幅高科技未来图景,凸显日臻完美的技术,却磨灭不了人性深处永恒的残缺。这大概也是人类对自身的检讨以及对未来技术的期许。但在当下世俗的法律世界里,冰冷的电脑界面还远未能取代庄严肃穆的法庭和威严睿智的法官。或许,我们往往执着于人性差异所可能带来的偏颇,却忽视了统一代码背后的僵化与冰冷。